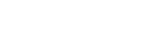一碗
我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心怀着一个疯狂的念想:每个人都可以写歌。
公鸭嗓的人写一首难听的歌,五音不全的人写一首跑调的歌,抑郁的人写一首很丧的歌,我们充分享受着创作的权利,像是学会文字的每个人都可以写作,音符也跟文字一样被放在一个储存库里,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将它们挑选摆放,写一首歌就像发一条朋友圈一样简单。
大部分勤学苦练的人不会赞同我,在挑战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时候,我也逐渐懂了些人情世故。
于是,这张专辑是一个总结,也是一个开始,这是一个关于包容的话题。
我幻想音乐是一个容器,可以盛饭,可以盛粥,可以盛茶,也可以盛酒,有人盛着鲍鱼海参,有人盛着小咸菜臭豆腐,每个人随意的挑选自己的口味,又不曾置喙他人。
在这里,它是一个碗,承载着所有的可能性。
公鸭嗓的人写一首难听的歌,五音不全的人写一首跑调的歌,抑郁的人写一首很丧的歌,我们充分享受着创作的权利,像是学会文字的每个人都可以写作,音符也跟文字一样被放在一个储存库里,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将它们挑选摆放,写一首歌就像发一条朋友圈一样简单。
大部分勤学苦练的人不会赞同我,在挑战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时候,我也逐渐懂了些人情世故。
于是,这张专辑是一个总结,也是一个开始,这是一个关于包容的话题。
我幻想音乐是一个容器,可以盛饭,可以盛粥,可以盛茶,也可以盛酒,有人盛着鲍鱼海参,有人盛着小咸菜臭豆腐,每个人随意的挑选自己的口味,又不曾置喙他人。
在这里,它是一个碗,承载着所有的可能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