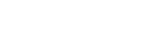珍珠走廊
我好像做了一场“不属于自己的梦”
梦里也守着西南的海,有银白的沙滩、有朦胧灯光…
而珍珠般的走廊的尽头,穷尽着我今世所有的欲望以及幻想,
向前一步、便拥有一些,再向前、再拥有…
直到“该有的”,我好像都有了。
可这场景总让人觉得熟悉,熟悉得就像个异乡…
尝试“睁眼前”的刺痛,跟努力“闭眼后”,好像都差不多。
而上一场清醒的最后一帧,头顶白色的追光做了闯入者,乐此不疲得剥夺着我的睡眠、我的光、我的热…
笔是我的,手却不是;话筒在眼前,喉咙却不在身体里;
欢呼和啸叫中,我和他们一样,都成了想象中了不起的大人物...
只是那束追光又摇了摇,晃醒了我
“要上台了,也该醒了”
“可我还是不能在床上断气”,
因为眼前的美好,没有味道。
纵使满嘴流油的亲戚远不如黑车司机了解我、纵使无尽的起落架总衔接话筒架、纵使我和他和她和它有时也没办法讲话。
纵使俱乐部里有一万种轰轰烈烈的死法,
“可我还是不能在床上断气”...
我们好像都做过“不属于自己的梦”,但梦,是没有味道的。
梦里也守着西南的海,有银白的沙滩、有朦胧灯光…
而珍珠般的走廊的尽头,穷尽着我今世所有的欲望以及幻想,
向前一步、便拥有一些,再向前、再拥有…
直到“该有的”,我好像都有了。
可这场景总让人觉得熟悉,熟悉得就像个异乡…
尝试“睁眼前”的刺痛,跟努力“闭眼后”,好像都差不多。
而上一场清醒的最后一帧,头顶白色的追光做了闯入者,乐此不疲得剥夺着我的睡眠、我的光、我的热…
笔是我的,手却不是;话筒在眼前,喉咙却不在身体里;
欢呼和啸叫中,我和他们一样,都成了想象中了不起的大人物...
只是那束追光又摇了摇,晃醒了我
“要上台了,也该醒了”
“可我还是不能在床上断气”,
因为眼前的美好,没有味道。
纵使满嘴流油的亲戚远不如黑车司机了解我、纵使无尽的起落架总衔接话筒架、纵使我和他和她和它有时也没办法讲话。
纵使俱乐部里有一万种轰轰烈烈的死法,
“可我还是不能在床上断气”...
我们好像都做过“不属于自己的梦”,但梦,是没有味道的。